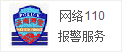四
乘格若拉姆姐姐的船下湖是在晴好的上午:阳光从东面山头上斜斜地铺半湖红亮,空气中融了熟透的苹果香味,醺醺地醉人。我们的船滑行在碧蓝的湖面。猪槽船是整木挖成,朴拙结实。湖面,平滑如绸;船行其上,只能说是滑了,被船牵皱的湖面,很快地又被绷平了,根本没有划的破痕;静静地,没有水声,更没有浪花。吉祥的白云,缠绕在高高的狮子山间,我不禁轻轻地哼起昨夜篝火晚会上格若拉姆教我的歌:“美丽的泸沽湖,迎来了朝霞;雄伟的狮子山,白云缭绕;善良的阿妈,为何您这样高兴,哎哎哎──哎哎,只因为女儿长成人啦,只因为女儿长成人。”
“在泸沽湖上,坐着这里特有的猪槽船,不与摩梭姑娘对歌么?”船到了阳光的湖面,格若拉姆的姐姐停了桨,拿热辣辣的目光向我挑战;一边已放开歌喉,唱起泸沽湖情歌。这是只有高原女儿才有的嘹亮,这是只有泸沽湖才有的甜润,这是只有摩梭女儿才有的热烈的纯情;山头的白云为之舒卷,岛上水鸟为之盘旋,渔人停了下网,远远地传来火热的对唱。歌声在湖面滑来滑去,深深的湖水也天空似地透明了。
我们被陶醉了:我轻轻地击着船弦,而吴小姐一直宁静地微笑着。我发现这个完全受西方教育的女子,在泸沽湖的这两天安静极了,脸上时时会罩着一种纯净的光辉。心与歌声、晴空、湖水一样透明了,只想像丝巾般的白云一样永远地泊在湖里。
还有什么可以顾忌的呢?我放开喉咙,一首接一首地唱出了自己所有会唱的情歌;而每一首,格若拉姆的姐姐都能接下去唱和。唱啊,唱!除了唱,还有什么能表达此时的心情!
一起游了里务比岛(摩梭语,意为菩萨岛)和黑挖务岛(摩梭语,意为中心岛)。船快速地向回滑行的时候,我们饶有兴致地和格若拉姆的姐姐开着玩笑,听她讲摩梭人走婚的故事。我问她:“你开始走婚了吗?”“我可以走婚了”,她说。吴小姐也情不自禁地用生硬的普通话问:“他(指我)也可以和你走婚吗?”“可以啊”,银铃般的笑声颤得船也摇晃起来。
到岸边的时候,我仍没忘吴小姐的那个问话,对格若拉姆的姐姐说:“晚上我去你那走婚。”
“先跟我弟弟一起打三年渔,等格若拉姆长大吧。上岸了。”
所有的玩笑都留在了泸沽湖里。
五
要在泸沽湖里游回泳,是我和吴小姐的共同的强烈愿望。午后两点,太阳无遮无掩地照着泸沽湖;湖面有了轻轻的风,亮亮地折射着强烈的阳光;虽已深秋,仍让人觉得醺醺地温暖。
泸沽湖向我们展示着她最亮丽最丰富的色彩:深深的蓝在向狮子山脚下延伸的时候,递换着湛蓝、墨蓝和苍黛的色彩;黑挖务岛那边又是夏天般的浓绿;向里务比岛方面的湖,是云的银灰和天空般明净的湖兰;我们正面的湖水又是一种只有背光的珍珠才有的灰;更有说也说不清,画也画不出的奇妙的色彩,而都明净地有质感。我们小心地向湖中走去,水虽然有了秋的凉,但舒爽极了,是被热恋的人假意冷落的感觉;下面是米粒似的栗色石子的底,轻轻地扎着脚板;水却不见一点浑;前边点的湖面有星星似的白色小花浮着。
我们整个地扑进去了,调皮地搅动;深深地扎下去又忽啦啦冒起来,水从吴小姐雪样白的背上滚落下来,一群浑圆调皮的珍珠。使劲地搅动啊,水像水银似的跳荡着一轮轮扩散;累了,躺在湖面看亮晃晃的天空,如儿时躺在母亲的摇篮。
格若拉姆在岸上拿我的傻瓜相机不住的按快门,也不知她会不会拍,我们只管游。
“来,到岸边让格若拉姆为我们好好拍张照吧”,我叫吴小姐。
“不。我会害羞。”她脸上还真的浮起了潮红。多想就一直泡在这明净的湖中啊。不经意里,天上下起了小雨,一种舒舒爽爽的透明的太阳雨,太阳仍明亮地照着。
“你看到了吗?虹!”吴小姐面向日增翁山(摩梭语,意为山神)对我说。
从日增翁山山腰处,一拱七彩的虹直架向湖对面去,我也正惊奇地发现这个事实。
“从虹上,我可以回四川了。”我忽然想起湖对面的母亲。
不知吴小姐是否能听懂我这句带了浓浓东方色彩的话?她给我说起过:加拿大孩子十六岁左右就几乎全部脱离了家庭。她读大学是自己向政府贷了二万加元(相当于人民币十二万),现在她每月要还的贷款相当于人民币一千三百元。她到中国旅游已近一年,说中国电话费太贵,很少给父母打电话,她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哥哥在干什么工作,大部分加拿大人离开父母工作了,是极少回家的。我与她说起这个话题时,她其实也有想看看父母的心情,但她的下一站是中国的桂林,然后去香港谋职,回去看父母还未上议事日程。
岸上的格若拉姆,永远也不会去想这样的问题。
六
泸沽湖的夜没有灯光,远远近近不会有一点昏黄,没有人声,没有犬吠,虽然格若拉姆家就分明地有一只极温顺的黑狗。只是一到晚上便有了浪,有浪豁──豁地涌向岸,象皮毛光滑的水獭,沿湖迅疾地向前窜去。似乎只有了湖的存在,它在入睡前的呼吸很急迫,急迫在一种祥和的宁静里。
今夜有月,是半块弦月,朗朗的清辉;高原不遵月明星稀的规矩,星星照样的繁密、闪亮,亲近着这美丽多情的泸沽湖。
我和吴小姐坐在湖边,或许这湖边就只有我们两人。一起的时间从丽江出发算起,已整整有四天了,明天,便会各自东西,但我们都没有分别的情绪。一起坐在这美丽的湖边,也仅仅是一起看各自的风景。静默的时间很多,说话的时间很少。
“你认为这里很美,是吗?”是她在泸沽湖来后多次的发问,其实我知道这是她对泸沽湖的肯定。应该说都对泸沽湖充满留恋,但留恋的仅仅是湖而已。
湖边疏疏爽爽的是低矮的栅栏似的杂树,高而成排的是杨树和树围绕的村庄,远一点的树冠浓浓的是我们每天都去打果子的核桃树;而湖,笼了秋月的轻雾,朦朦神秘地美丽;湖中里务比岛和黑挖务岛是月下能看到的剪影。
“今天格若拉姆送你的彩色线织腰带很美,是吗?”
“她说是她学会织的第一条腰带。”
“她是爱上你了呢。”
“但她才是十四岁的女孩子。”
“这里的女孩子象我们加拿大女孩一样大方热情。”
想起格若拉姆送我腰带的样子,就觉得有些愉快的想笑的感觉,但如果我现在才十几岁,真要去跟她哥哥一起打三年鱼!
明天要赶这里现在每天唯一的一趟去宁蒗的早班车,我们便早早地转回迪尔阿妈(汉姓曹)家了。打开我住的房间,吴小姐也跟了进来。本来她住在我隔壁,虽然晚上她到我房间坐坐,谈会话是自然的事,但今夜分明有点异样,她的行礼就放有对面床上了。
“我忘了告诉你了,下午你和格若拉姆去湖边剖鱼的时候,这里又来了客人,迪尔阿妈说我们的房间都要住进别的客人,我便搬到你这边来了。”
“这可以吗?”
“可以。”
“但按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是不行的,因为只有夫妻能一屋住的。”和她说话,我已习惯按她的直接方式了。
“但我们不:这间屋子里有两个床铺,与一个单间里一张宽大的床表示的意思不一样;我们在旅游中,因为房间太贵,常常与同行的朋友合租双人间或其它;但是对不起,我第一次和中国男孩结伴同游,也许不知道你们的习惯。”
“听说你们在性方面很随意,是吗?”
“我们在性方面有我们的自由,因为结婚的时候,没有哪个男人会问女的是不是处女。但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:我们受基督的约束,我们觉得事后避孕是不道德的;现在都对自己的健康很看重,怕染上病;虽然我们的女人生了孩子,不会有人笑话,也不会为孩子的出生证明担心,但孩子没有父亲是不行的;我们很看重感情,泸沽湖的人像我们那里。我们明天都分别了,是吗?你能明白我的意思,是吗?”
当然我不愿把泸沽湖和她们加拿大的道德行为习惯扯在一起,虽然起点和终点可能是同一个地方,但谁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。我只咕噜了句:“自由中的不自由和不自由中的自由当同是一种境界。”
“你说的是什么意思?”
“我没有能力为你解释这句话,因为我们语言中有些障碍我不能克服。睡吧。”
泸沽湖的浪喧得更响了,但除了浪,宁静得没有一点声音。我知道摩梭男人开始走婚了,而狗,或许正静静地帮它主人等那个熟悉的推门声。
月光在这木屋里划开一道两尺宽的河,木墙、木顶、木地板散发出的好闻的气息里又多了另一种气息。
到这该结束的时候,我倒有些为难了:如果不宣染一番“我作为一个血性男人……”怕读者给我一顶道学家的帽子,也怕被高举中国“食色性”文化的人们批一句“有缺陷”……
事实是:对面那张脸泛着恬静的月光,轻轻的均匀的呼吸与泸沽湖的月融在一起。听着那平静的呼吸,我却如闻临济禅师的吆喝!湖里的浪声正渐去渐远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