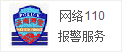去的路上一直担心是否能够进藏,沿途果然有关卡,原则上不放游客进藏。第一个关口秋那桶,我们说要在秋那桶过夜,明天回,拿着身份证下车登记就放行了。这个关口,有比较正规的办公室,路面设一根拦截车辆可起放的油漆木杆,就是上海住宅小区大门在没有自动移动设施前那种拦截车辆的木杆。
过第二个关口松塔,大约是中午的样子,崎岖狭窄的山路上横着一根简易的木杆,木杆本身呈木自然色,旁边有个简陋的屋子,我们的车子停靠了一会儿,没有任何人出现,按了车上的喇叭后,从旁边的山坡上缓缓走下来一个中年男子,头发蓬乱,面容疲倦,简单地寒暄了一下,就立起木杆放我们通过了,好简单哦!
第三个关口喇嘛寺已经很接近察瓦龙了,这个关口查得很严,我当时感觉要被原路赶回去了,他们说现在游客不可以进藏,因为有很多记者不怀好意到西藏,拍很多负面的照片,我们说我们只是到四川饭店给老板送点菜,不是去旅游更不是记者,他们围着车子,透过窗子,说:你们带了相机吧,我们没有说话,他们又说,带相机就不能进去,而且四川饭店老板叫什么,你们也说不出吧,所以你们也不是去看朋友。。。磨了很久,最后让我们下车带着身份证登记,反复叮嘱,在察瓦龙不允许拍照到处走动,只能在四川饭店停留,放我们进去对他们来说风险很大,搞不好要被开除的,他们都是国家工作人员,被开除就没有饭碗了。
那条路上的四川人
到达察瓦龙,蚂蟥熟门熟路地和四川饭店老板寒暄问候。四川饭店的老板自然是四川人,一家三口在一起经营这个提供吃住的四川饭店,住处其实就是一个楼面用三夹板隔出的几个单间,没有卫生间浴室,每晚按床位收钱25元。
看架势,老板是接受过专业厨师训练的,他给我们烧了二条江鱼,当天刚进的货,老板把江鱼新鲜滑柔的质地全保留下来了,这是我们后来在别的地方吃江鱼时才意识到的,同样是当天新鲜的江鱼,四川饭店老板烧的水平相当不错。
他一边熟练地炒菜,一边和我们聊天,他告诉我们,本来在四川过得还可以,有个亲戚在这里驻边的武警部队当领导,他们两口子就过来了,如果没有亲戚在这里,打死也不会过来的。中国的血缘文化很神奇,血缘带动着人们的地缘迁徙,人们的地缘迁徙又带动着血缘的迁徙,四川人遍布中华大地角角落落,甚至察瓦龙这样偏僻的乡村。
老板的大儿子最近刚从四川过来,小家伙初中毕业,不愿意继续读书,就过来帮父母做事情,长相和打扮很像当红歌星林俊杰,前刘海和后脑勺的头发故意留得长一些,抹上发胶的发梢亮亮挺挺的,好像刚刚洗过,圆嘟嘟的面庞总带着微笑,不高的身材因时髦前卫的装扮显得挺拔帅气。
我们问老板察瓦龙没有蔬菜、豆腐之类的,他开个饭店等于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,他说,平时自己去进货,啊,到哪里进货?丙中洛。丙中洛?那么远怎么去?摩托车。摩托车拉不了多少菜吧?还可以,100多斤当天来回!哇,太惊人了!我们坐在SUV里折腾一天,惊险无比,过大流沙,累惨!老板自己摩托车当天来回加100多斤菜。。。哇!
路上还看到一个骑摩托车的人,在雨里,和我们在狭窄的山路上一前一后,我们在龙坡村停下来时,他问要不要江鱼,他那天捕了二条江鱼,穿着雨靴,全身溅满了泥点,脸庞红彤彤,那种高原红,他是专业捕江鱼的,一天捕个一二条,维持生计,他是四川人!
四川人总在创造着奇迹!中国人为了生存总在创造着奇迹!别看我们这帮人,假模假势的,真到了和四川饭店老板的生存状态,兴许完全可能做出同样的事情,人为了生存可以爆发巨大的潜能,尤其是中国人!这恐怕和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基因有关,不能长期拥有安宁的民族总在居安思危的状态,万一有一天危出来了,几代几十代几百代储存在身体的那些基因就会发挥作用。四川人正在用他们一手一脚做出来的事情告诉我们这个真理!
察瓦龙及那里的人们
察瓦龙是西藏自治区林芝州察隅县的一个乡,察隅县曾经在麦克马洪线时被划在印度,后又回归中国。五十年代初,解放军进藏曾从丙中洛入察瓦龙进藏。
察瓦龙地处怒江上游,干旱炎热,周围的山光秃秃的,经当地人指点,的确山里有“蛇”,大山的形状如蛇。这里,2005年底才通路/车(往丙中洛),2006年才有电,2007年通电话。记得2002年在丽江时,了解到附近的宝山石城1999年底才通电,我惊讶不已,察瓦龙的状况,比宝山石城还要晚好多年。
阿皮
刚到四川饭店,蚂蟥就说他的好朋友、“亲家”阿皮,在里面搓麻将,亲家之所以加引号,是因为蚂蟥未经自己二十多岁的儿子同意,预定阿皮家还在读小学六年级的三女儿当儿媳。
蚂蟥说阿皮傻乎乎的,老在这里搓麻将,人家在算计他,他肯定输嘛,也不好直接讲给他听,只能提醒他不要老搓麻将,他还不听,今天肯定又输掉很多,藏人有时就是傻。我不禁想起南怀瑾说过,我们汉族人因为缺乏忠孝仁义,老祖宗几千年前就教导我们要忠孝仁义,南师说他曾在边疆工作,边民很反感汉人,我们汉人觉得边民野蛮怕我们占地盘所以不接受汉人,其实汉人在边疆做了不少坏事,把边民都带坏了,让边民讨厌了。我特别有同感,这几年在西部游走,发现汉人出入的地方,风气就坏,而汉人又“无孔不入”,我就是汉人。面对蚂蟥的阿皮输麻将说,我只能内心道惭愧惭愧!
蚂蟥晚上带我们到阿皮家串门,在黑黑的村路上,我们打着手电筒,深一脚浅一脚走着,见了玛尼堆顺时针转,路经藏民家,无一例外都引来无数咆哮的狗叫声,放眼望去,除了夜的黑就是大山的黑,黑压压笼罩着四周、卷裹着我们,狗叫声伴着我们急促、深浅的脚步声和喘息声,很特别的感觉,到现在回忆起来,依然别有一番滋味泛上心头。
阿皮家的房子很大,我们在堂屋里坐下来,阿皮家人给我们倒青稞酒,和拉萨喝的不一样,这是自家酿的,有米酒那样的混浊,度数不高。房间里有个电视,电压不稳,一会儿电视没人影儿了,一会儿又好了,大家都没有在看电视;我们几个在聊天,阿皮家祖孙四代在另一个角落席地而坐,低声温和地讲着话嬉笑着,看着他们一家亲热的样子,想起久违的七十年代没有电视全家晚上围坐一起聊天的景象,身上涌出一股暖流,眼睛也热了一下;家人之间的温暖不需要电视,电视把世界拉近到我们眼前,电视也给我们制造距离,人和人之间心的距离,远了。
阿皮家刚添了第四代,阿皮当爷爷了!阿皮本人才三十多岁看上去还是小伙子一个!阿皮的大女儿出落得很漂亮,那种细嫩欲滴般鲜花的美丽,刚当妈妈的她,身材苗条圆润挺拔,椭圆的脸庞线条柔和,鼻梁坚挺,眉眼妩媚,看上去还是小姑娘,言谈举止中流露出女人的韵味。上门女婿是察瓦龙乡武装部部长、察隅县驻察瓦龙乡公安局特派员,小伙子个子不高满脸黝黑,身体结实面部严肃老成。他九岁就到内地接受教育,在哈尔滨、武汉等地学习生活过,随身带的手提电脑里存着《德拉姆》,我们到了以后,他就用电脑放着《德拉姆》,说着田壮壮当年在察瓦龙拍片的趣事。
在内地接受过教育年轻的武装部部长,告诉我们,他户口在北京,但是他不打算让他的孩子成为城市户口,因为有西藏乡村户籍可以享受很多优惠政策,很优越的条件,比如孩子上学不要交钱,政府还倒着发钱。
年轻的副乡长
我们在四川饭店晚餐时,进来一个满口东北大茬子腔的高个小伙子,面孔黝红,精干壮实,言谈中略显腼腆,他和我们说,蚂蟥哥可是丙中洛的招牌、驰名商标、旅游形象代言人!
小伙子大学刚毕业一年,女朋友是云南人,跟着女朋友从大东北来到云南,怎么进了西藏?西藏不是想进就可以进得了的,要经过组织上层层审核,小伙子很骄傲地说。那平时干什么呢?下乡,骑着毛驴下乡,察瓦龙乡管辖的村子可分散了,下一次乡坐着毛驴走不少山路,刚开始,到了村子从毛驴上下来,才发现,长这么大从来没有感觉,那么强烈地感觉到,原来屁股是两瓣儿的,走山路颠出的感觉。
在这儿干挺锻炼人的!他说着,我们用赞赏的目光望着他,在他身上几乎看不出学生气,很老成的样子,很有思想的样子,环境锻炼人哪!将来的发展方向?往县里发展呗,察隅县!他不加任何思索果断地说。需要多长时间呢?不管那么多,慢慢磨,时间要慢慢磨,人生也要慢慢磨!他说这话时,那个磨字三次从他的舌头、牙缝、唇间狠狠地磨出来,这几句话本身就是在艰苦条件下磨出来的!看到他坚毅的神态,我们对八0后肃然起敬!中国有戏!
山东老乡
年轻小伙儿,很帅,黑红黑红的脸,讲话的腔调很西藏味儿,刚见他时,听他一个字一个字地往外蹦汉话,很不不熟练的样子,觉得他就是察瓦龙人,察瓦龙人长得漂亮,男人帅女人美。
结果人家和我们一样是汉人,在西藏当兵,就地复员成了公务员,回老家不一定能当公务员。见面那天他刚好发烧,人昏沉沉地还在上班,当我说“能请教你一个问题吗?”,同伴悄悄地用腿砸我,肯定是担心我随便和藏民侃大山,惹毛了人家不好办,结果我问“你多大了”,他腼腆一笑。
聊着聊着,发现原来他是汉人而且是山东人,同伴正好也是山东人,用带着山东煎饼味的家乡话喊了声“老乡”,小伙儿刹那眼泪都快出来了!“想家”!真正是“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”!同伴第二天一大早,整理行李时,坚决地决定将从北京不远千里带来的速溶咖啡,全部留给老乡,仗义!
关于白马校长的传说
在察瓦龙的第二天清晨,我们在四川饭店门口见到了传说中的白马校长。白马毕业于拉萨师范大学,是四川饭店对面察瓦龙中心小学的校长。察瓦龙中心小学是一个寄宿制学校,察瓦龙乡管辖村寨的孩子们,三年级以后都要到察瓦龙寄宿上学,包括我们提到的龙坡小学的学生。《德拉姆》里面那位美丽的乡村代课女教师就是察瓦龙中心小学的。
白马高大魁梧,面庞饱满黝红,气质斯文。在来的路上听说他不当校长了,不当的原因不知道,但他这个校长有时当有时不当,不是他自己可以决定的,主要是乡政府那边的决定。关于白马的传说,和上海的一位姑娘晓帆有关系。
晓帆,不到三十岁,独自包车从丙中洛到察瓦龙,在返回时,司机问晓帆是否可以,白马和他的舅舅要搭车去丙中洛,晓帆同意。一路上,大家没有很多的交流,中途晓帆下车拍照,临回车上时发现镜头盖找不到了,司机和白马帮着到处找,最后白马找到了,将镜头盖交给晓帆。接着依然是一路无语,大家在丙中洛分手再见。
没有想到,就是这一路的无语,擦出了白马和晓帆之间爱的火花,二人陷入爱河不能自拔,晓帆决定嫁给白马。晓帆返回上海后,二人书信往来密切。
突然,白马和晓帆断了联系,晓帆所有的书信如石沉大海。。。晓帆千里迢迢找过来,带着上海热心朋友们捐赠的书,打算捐给白马的察瓦龙小学,可是晓帆在丙中洛等白马,等啊等,不见白马的身影。晓帆知道白马不会来了,将书籍捐给丙中洛的学校,伤心地返回上海。
有人问白马,那么痴心的姑娘,为什么要伤她的心,白马说正是爱她,才去伤她的心,他是偏僻山村的小学校长,而姑娘是上海大都市的白领,二人根本不是一个世界的,能有一段感情他已经心满意足了,但他不能为了自己,自私地企望永远占有姑娘的感情,尚且他也清楚地认识到这段感情在现实中不可能永远。。。
这个“世界是平的”,穿过崎岖惊险的山路,貌似偏僻的山乡里,和外界一样,天天都有感情产生着、消失着,都有故事发生着、被忘记着,白马在城市接受过教育后选择了山乡,因此也选择了生活方式,这样的生活方式自然地帮他决定了他的未来,包括未来的生活伴侣。在整个选择和决定的过程中,白马够男人!
察瓦龙视角
在察瓦龙听到一些故事和议论,内容和结局让我们始未料及。
关于文成公主,他们认为文成公主确实给藏区的发展带来了文明。但是文成公主在西藏不是很受爱戴,尤其是后来她失宠了,被贬到青海终老其身。汉人可能都不了解这个情况。听藏人说的时候,感觉像真的一样,虽然说者和听者与文成公主她老人家都不认得,也不沾亲带故,更是距离久远久远。。。
关于班禅,他们认为藏人的政治和宗教的最高领袖只有一个,就是达赖。班禅是汉人弄出来的,什么班禅管理后藏,达赖管理前藏,二个人平级,实际情况不是汉人说的那样。藏人心中的领袖,只有达赖。虽然我们阅读过一些有关的书籍,了解不同的说法,但亲耳听到藏人亲口说出来的观点,大脑还是受到冲击的。
关于山里看不见的神灵,他们说前几年从上海来了个推销员,到察瓦龙推销电热水器,结果察瓦龙没有人买,他很沮丧,问村里的人怎么走出大山,然后就离开了;不久,有人发现他用自己的裤带上吊在一棵树上,在深山里。村里人说,估计是夜里在山上看见了什么,吓死的!据说因为这桩人命案,当地出动了很大的警力调查,判断是否有他杀的可能。我们听后赶紧说,可能是温州的推销员吧,上海人不会跑这么远卖电热水器的。谁知道!
关于怒江水电开发,很多专家反对,不仅是因为邻国的政治问题,怒江是条国际河流,我们在上游搞水电,势必会影响下游国家,同时还是关乎生态保护的重大问题,怒江沿线的生态原始但脆弱,做出开发的决定要慎之又慎。可是当地人说,为了生态就牺牲我们察瓦龙,我们没有更多的电可以用,也因为没有更多的电就没有更大的发展,我们就因此永远原始落后下去,这是不公平的!的确,站在察瓦龙人的角度,他们的说法不无道理,可是他们如此说法话音刚落,汶川地震,《中国国家地理—地震专辑》就提出了水电对环境的破坏以及对地质结构的破坏,直接受害的其实还是当地人。人生最大的难题就是取舍,取舍是怒江沿线水电建设与否的主题。
关于领工资,察瓦龙是乡级单位,在这里工作着很多有工资的国家公务员,他们每个月都有工资,但拿不到。察瓦龙没有银行或者银行的自动取款机,交通又很不方便。他们每个月的工资都打在银行的卡里,在云南贡山县银行卡里。过个半年,花二天时间,走过那条崎岖惊险的路,去贡山县城“领工资”,这是在现代社会罕见的生活方式,貌似古老的传说。
关于开发旅游,据说云南贡山县每年的政府旅游接待费300万元,吃都吃不掉,遇到附近乡县的干部到县城,县干部拉着就进馆子,开发旅游招待餐,吃300元,发票开成600元,既完成了旅游接待任务,又拉近了各地干部与县干部的感情距离,还能多报销钱。我们只是听说,而且不只在一个地方听说。这个传说,特别在我们面对沿途孩子们渴望的眼神时,敲打着我们的心!疼!
从察瓦龙回到丙中洛的那天夜里,我的腿上出现了20多个新鲜的大红疙瘩,奇痒,一直痒到上海,哈哈,臭虫给我留下鲜血凝成的难忘礼物!
摘自田壮壮,居住在这里的民族,就像高原的山脉,不卑不亢,充满神奇般的色彩,与自然和谐地并存---我们这些从外边来的人,只能仰视他们、欣赏他们、赞美他们---这里能够给你一种力量,一份祥和及发自内心的喜悦,他们并不会因为你的赞美而改变自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