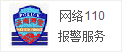2003年2月7日,农历正月初七,我去了绮罗。出腾冲县城,沿热海路往东南方向,行未远,路边一干净小店。绮罗多远?“这里就是绮罗了。”穿白色工作服的清秀女孩,笑起来如阳光下朴素的白雪。空气安静,有草的香。
小店门窗用料极为考究,是那种带有好看花纹的楸木。雕花的窗子。斜射的阳光懒散地穿过,店内地面上长出云团似的文饰图案。门贴大红春联:一碗饵丝两壶酒,三分孔孟七分庄。大灶炒菜的厨师,便是写春联的人。再问文昌宫在哪里?
水映寺在哪里?和气地笑,在下绮罗,前面不远,看见几棵古树就是。
绮罗分上下绮罗,分界是几棵上了年纪的老树。
几棵老树,抖擞的绿,枝桠错节如清水中盛开的墨华,数人合抱的树干,圈红色的纸带。新春“挂红”祈福,腾越人世代流传的旧俗。
撇开柏油公路,走一条杂草的路。田坝整齐平整,恍眼间隐隐约约飘着茸茸的绿,种子萌芽,大地回春,散步的鹭鸶,乍然振翅,迎着风飞,阳光被搅得灵动起来。田里拉下的一只,细长的腿,独立如荷,头藏在翅膀下,倒像是睡着了。
路一转,一条小河突然就撞到脚边。河水浅,卵石可数。路与河埂合二为一。河柳分行,数千棵柳树沿河两边迤俪而去。柳树还没有发叶,枝条却已经变软,将舞未舞,撩人情思。
村落,往往是以宁静安详的姿态出现。鸡声。人迹。青色的瓦。檐上的草。
我在绮罗转悠。看天,呼吸。游手好闲。我想不起有什么事这一生一定要去做。
两个老人在小卖铺前下棋,慢吞吞地落子。大口径的搪瓷缸子,浓茶,色泽发黑,自己喝,对手也喝。老板伏在柜台上打瞌睡,红糖、盐巴、爆竹、各种包装精美的零食,电视重播春节联欢晚会,演员拙劣地搞笑。小孩,穿灯芯绒的新衣服,笑出了口水。都是日常生活的细节。有人下棋,有人睡觉。有人老去,有孩子长大。有人出门,有人归来,很多生命在自家的屋檐下,很多屋檐连在一起。
小小的四合院。正房、厢房、厨房。土基围墙。正房的堂屋里,供着天地牌位:天地国亲师。一位老妇人走出来,满头银发,面目清秀,像童话中的外婆。“来坐,来坐,”也不问客人从哪儿来,转身自顾倒茶去了。干净的小院,铺水泥地皮。照壁前,香橼树叶片肥厚。挂满枝头的香橼,温暖的金黄色,在阳光里如大块金子拧成的团。
老人叫诺布其春,藏族,78岁。50多年前离开西藏,随丈夫来到这里。一个普通的农家小院里,藏着驿路古道的传奇。绮罗小伙子李和仁到西藏做生意,结识了藏族商人的女儿诺布其春,两人一起经营当年在腾冲很有些名气的贸恒商号,茶叶、土特产品卖到缅甸、印度,棉花、棉纱、洋货运来云南,边城小村做起跨国生意,老人会讲藏语,腾冲土话,还通缅甸语、印度语和英语。
出了老人家,看小巷里石板,不知道那些凸凹不平的痕迹,是否是马蹄踩出来的。不知道这些四通八达的小巷,是否是香橼树的枝条。
她的果实,走遍天下。
忽然就想在绮罗住下来,在自己房屋的周围种下很多香橼树。叶片清香,不生虫。果实和书本放在一起。黄金的血缘和生命的思想。
走遍天下。叶落归根。
绮罗有几条小巷,就有几个“大门”。
一条小巷住的往往是同姓的人,朝前数几代,还是沾亲带故的关系。巷口共用的“大门”,圆拱形门洞,火山石堆砌的墙,流风挂云的飞檐。“大门”是一个家族的标志,自然要体面些。一条小巷十几户或几十户人家,某姓人进出某条小巷公共的“大门”,无意中,就自己的“根”,作出了乡土的指任和判断。
“大门”外是路。路通天下。出门读书的、做官的、打工的、经商的,旧社会“穷走夷方急走场”的,都从这里启程。欢怨离逢,衣锦还乡。一个老人告诉我,从这些“大门”走出去的绮罗人,无论多么显达、富贵,都会回来,不会忘记自己姓什么。
我的手上有一份过时的统计资料,据下绮罗村1988年的侨情普查,全村在国外的华侨956人,外籍华人854人,分布在7个国家和地区。全村的归侨、侨眷408户,2077人,占总户数的61.5%。事实上,我不看这些数字,我只要闭上眼睛,耳边就会响起丁冬的铜铃声。丁冬丁冬,从某个时光的深处,牵出一队马帮,西南丝绸古道的风雨泥泞里,早就飘摇着绮罗人模糊的背影。
关于马帮的故事,关于古道的兴衰,今天已经有很多专家学者在发掘、论述,我不想在赘言。我在绮罗闲逛的时候,我只是想起那些哀怨的女人,和她们那么幸福的守望。她们是马锅头的魂,是古道的延伸,是人性极大值的压缩、扭曲,也是灿烂如花的释放。绮罗旧语:有女莫嫁绮罗乡,十年守寡半年双。那些出门谋生的汉子,唱着赶马调,在深山老林里做着发财的梦,梦见给自家的女人买光鲜的衣服,上好的翡翠镯子。而那些守在家中的女人,从某个天不亮的早上,把丈夫送出门,她们的等待,就比古道还长。
以后的日子,孝敬老人,抚养孩子,耕田种地。男人挑的担子也挑起来。肩膀宽了,脚大了,青春不在了。月缺月圆,总是空荡荡的夜。无数个早晨或傍晚,洗衣亭边重复着这样的对话。你家汉子带信来了?不有。怕早喂豺狗了。你家的呢?也不有。洗衣亭的水搅得哗哗响。我在一个小巷的“大门”下,久久地站着。我看见风穿过“大门”,风中寂灭了灯花般的叹息。
三百余年前,两个人走进下绮罗村的玉虎巷。一个是李虎变,一个是徐霞客。
李虎变,学名李正邦,虎变为乳名。相传其父乐善好施,一日赴鹤庆贩酒回程途中遇白虎,虎不伤人,围绕三圈后化为白银。李家由此发迹,感念神灵而为长子取名“虎变”。如果仅仅是这些民间的敷衍演义,李虎变的名字恐怕早已在风中漫漶流散。而幸运的是,他遇到了徐霞客。
明崇祯十二年(公元1639年)
农历五月初二,州痒彦李虎变到县城拜会了游历腾越的徐霞客。“痒彦”是一种学位,相当于今天的高中、中专。我不知道一个高中生去拜访徐霞客,他说了些什么,但我想他们一定谈得非常投机。徐霞客甚至愿意停下他匆匆的脚步,他答应了李的邀请,到绮罗小住。五月初四,李虎变亲自到县城接徐,“时微雨,遂与之联骑,由来凤山东南麓循之南,六里,抵绮罗”,“是夜,宿李君家”,徐霞客到绮罗,共七天,住李虎变家四夜。
霏霏微雨,洗尽轻尘。绮罗迎来了一个集地理学家、旅行家、文学家于一身的“千古奇人”。几百年以后,在他的那些流传世间的“真文字,大文字”里,我看到他饱含情感的记述。“绮罗,志作矣罗,其村颇盛,西倚来凤山,南瞰水尾山,当两山夹凑间”,“竹树扶疏,田壑纡错,亦一幽境”。绮罗的山水,从此活起来,在中国的文化史、地理史里。不厚重,但深远,以致我今天叩访绮罗的时候,我感觉自己的目光抚摩的是“时间的风景”。
走进绮罗文昌宫,我把脚步放得很轻。
任何一个接触腾越文化的人,目光都无法绕开那些一度在腾冲繁盛无比的文昌宫。明、清以来,腾冲各地大都建有文昌宫,供奉专司文运的文昌帝君。文运繁昌,山水清秀,人物才俊。民间还有“命带文昌”的说法,“命带文昌”的人,长大后读书一定非常成器。农、商为本的边地小城,却以“文运”为脉,耐人寻味。事实上,很多腾冲人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文化优越感和书卷气质。我认识一个腾冲籍的老教授,学理工科,搞了一辈子的建筑设计,不乏经典之作。自己引为得意的,却是闲暇时间“不务正业”编撰的三卷古诗词集注。我不知道他的生命底色里是否耸立着一个文运转承的宫殿。牌坊式大门。旧时学宫里常有的泮池。大块石头镶成围廊。图案花纹的色彩和线条已经模糊不清。池里的水浑浊不堪,拥挤着浮萍如杂物。几片睡莲的叶子费力地挤出来,像几张肮脏的脸。四百多年的风雨,神灵的家也已经没落。
过泮池,前楼两厢板壁。整木雕刻一米有余的两个字:“忠”、“孝”。正殿、启圣楼、后花园等建筑,南北纵轴,依次排列。魁阁、神祠等附属建筑分前布后,各自构成四合院的建筑单元。主体建筑为启圣楼。面阔三间,重檐,梁檐柱子描绘有花草,饰于浮雕和透雕文饰;六面格扇大门,团花棂子的背景,透雕施彩成图。图案内容取材于历史传说,分别是“明刑弼教”、“范公书院”、“历代义门”、“提戈取印”、“董昭救蚁”、“裴度还带”。几个故事都透着儒家文化的气息,例如“裴度还带”,讲的是有僧人为裴度看相,说他必定一生潦倒。数日后再遇,僧人大吃一惊,裴度的面相竟然在不知不觉中起了某种奇异地变化,将来出将入相,前程不可限量。原来裴度日前拾到了一条价值连城的玉带,不贪,还了失主。绮罗人农商并重,人生哲学的第一课,却是建构“重义轻利”的精神人格。
整个文昌宫采用文庙规制,周边红墙圈围。在神灵没落的家,我静静地倾听着仿佛还在风里朗朗的百年前的读书声。文昌宫的建造,不仅仅是供奉神灵的场所,它还是古代的学校,是养育精神和人格的园地。绮罗人的先辈们,在这里浸染传统文化的精髓,书写着一个大大的“儒”字。在我看到的许多资料里,对绮罗文昌宫的介绍,往往仅限于“古代文物”或建筑学的层面,无异舍本求末,买椟还珠。绮罗文昌宫的真正价值在于,它永远滋养着田野山村的人们的精神人格,最后生长“穷则独善其身,达则兼济天下”的理想主义。不信,你听那朗朗的书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