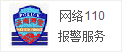早就听说瑞丽境内有座景颇人聚集的雷公山,山势雄伟、山色瑰丽,据说山上还有“仙人脚迹”呢!
于是,在一个天气晴朗的早晨,我们在一个叫腊排的景颇族汉子引导下,向雷公山进发。
除腊排左挂一把长刀、右挂一个大麻布筒帕之外,我们其他人都是两手空空,只有除人手一根就地取材的拐杖。山是层层叠叠的,远不是遥远处看到的那么单薄。歇气的时候,腊排总要唱上几句山歌。山歌应了对面山壁回过声来,十分空旷辽远,十分动听。那效果不亚于环绕立体声,而且作为大自然的造化,它近乎天籁了。每每这时,我们也就咿咿呀呀地跟着吼起来,无拘无束,疲累全被抛之脑后。有时,腊排的山歌被远远近近山头上歇活的人们听到,便三山五岭地应和起来,男男女女的,用唱的方式一对一答,可热闹了!不过,这种时候,我们就不敢乱唱了,也不会唱,真正地是个山的观客游人。哪像腊排,在山头的最显眼处,打个盘腿坐下,应对自若,一副山的主人气派。
一路上,腊排告诉我,景颇山寨里很多婚姻是对山歌对成的。男女各坐一个山头,越唱越显知音,越唱越情投意合,也越唱越走近,两人就永不分离了。
多么浪漫的爱情啊!无须厚妆重奁,无须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,一切陈旧的形式都简化了。爱情不用谈,而是唱,内亦即形式,真正达到爱情的本质。一路上,我情不自禁地往头的最高处坐一会,仿佛还有丝缕爱情故事的余温。我终于明白,景颇人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家园一个个筑垒在山头上了!
大约爬了六、七个山头,肚里有些咕咕叫了,可雷公主峰仍在遥远处,顿觉四肢无力起来。同行的杨斌过来拍我的肩:“你看前边,炊烟!”我们一伙人把埋在脚尖的眼光倏地抬起来,眼睛一下被炊烟擦亮:腊排在前边生火做饭了!
腊排无声息地忙乎着,不要我们相帮。他抽出腰间的长刀,一会儿砍来竹子,一会儿砍来砧板和芭蕉叶。然后把竹子砍成竹筒,用叶子把米包好放进竹筒,再把芜荽、花椒、大蒜、葱、姜一一变戏法似地从口袋里拿出来。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野的,是腊排一路上东扯一把、西抓一撮得来的。
不到半小时,腊排的竹筒饭菜焖熟了。他把竹子掏空,连节排列,把饭菜盛在里边,这叫“共筒(共同)”。正吃着,路边走来两个抬掼盆上山的景颇汉子。腊排用景颇话一吆喝,两人就歇下,坐到我们身边一同进餐,免去了一切推让之礼,吃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。
吃罢午饭,我们在一个山头找到了“仙人脚迹”,那是一块醋似脚板的磊石面,“纹路”经风雨剥蚀变得有些抽象,使其更有一种种秘感。我们把自己打了泡的脚板在仙人脚迹上量了量,一沾仙气。腊排告诉我们,这是仙人的左脚迹,右脚迹在缅甸南坎呢!嗬,步子跨得好大!一步就越了国界。
从仙人脚迹所在的山头走去、不远处就是雷公山主峰了。杨斌指指主峰旁的一间依稀可见的房了说:“那就是头人木东家,我们的宿营地!”
晚上,我们坐在木东家的火塘边,大碗喝着水酒和雷响茶,远远近近的灯火都在我们脚下,大有一种“会当凌绝顶,一览众山小”的感觉。主人木东,满面沧桑却一脸和善,话不多,汉语更不顺当,一任给我们沏茶盛酒。木东有两个儿子,一个大学毕业,一个当老板。儿子们都邀请他去城里住下,他就是不肯。倒是每逢年节,儿子们都要回景颇山几天。
一个民族与一座山,这种关系已经凝成一种信念。难怪老木东面对儿子的请求时只说了一句话:“儿呀,搬得了家却搬不走山!”